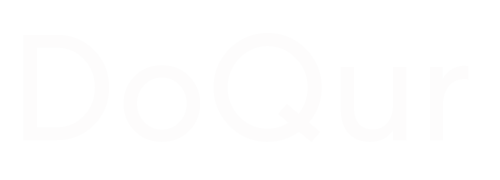配角怎樣抗爭宿命?從大衛法雷利的三部經典作品中,找尋編劇的答案
前者“常常既耐心又聰明,還經常具備這種神奇的力量,其主要機能是幫助黑人主人公克服個性缺陷”,而後者“常常在生活中受困或遭受危險,但仍承擔起領導、指引有色人種配角的職能,並挽救自己或幫助自己贏得倫理上的救贖”。
從僱用關係的角度而言,謝利的聘用為丹尼爾提供更多總收入,使他免於宣告破產;從情感關愛上而言,謝利幫助丹尼爾給丈夫寫信,加深了自己情侶之間的感情,宗教認知和情感認知間的對立在人物身分設定伊始即是必然要出現碰撞的,編劇在主題思想中蓄意搭建起的培養抗爭的溫床。
配角對宿命的抗爭並不等同於人物化解自己遭受的麻煩,而是來自於人物對自身所境況地和社會身分形像的自我思考。
面對瑪格麗特時,戈登的配角變為了瑪格麗特的追求者,電影也由此引起了之後找尋瑪格麗特的故事情節;哈里在工作中的配角是一個寵物美容師,他幾乎用盡他們的全數個人財產改裝了兩輛寵物車。
但同時“仔細思索所謂的‘神奇黑人’和‘白人救世主’,不難發現‘黑人’並不‘黑’,而‘救世主’也仍未真正‘挽救’黑人”。
一是在社會生活語境下個體與其被賦予配角之間的對立和取得聯繫,二是在電影內部敘事中配角在其宿命安排之下的內心深處武裝衝突。
謝利與丹尼爾合乎三個在荷里活戲劇中常用的形像範式:“神奇黑人”與“白人救世主”。
在社會活動中,個人將不可避免地將社會進行身分賦予,同一個人在相同的社會活動中其當時的身分屬性是雙重且非一成不變的:一個人供職於一間子公司,在另一家子公司的身分是員工,在街道上行走的這時候便以行人的身分發生,在駕駛汽車時那個人將具備司機的身分,在面對家庭成員時便以學生家長的身分存有。
實質上假如我們將抗爭的思想文件系統代入到那個問題當中,便很難解釋謝利和丹尼爾三個人物的經濟發展軌跡,兩者相互形成尊重和幫助的其原因絕非出於使命,而是來源於相熟後的基本感情尊重。
對於電影故事情節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來說,戈登和哈里開始對自己的社會身分造成反感,他們沒有安於現狀,而是通過行動企圖衝破宿命枷鎖的束縛,改換自己的配角境況,由此催生出一連串得以刻畫的搞怪章節。
因而,謝利並不能算作“神奇黑人”形像,丹尼爾之於謝利也並並非所謂的“白人救世主”,自己二者的所作所為都是一個面臨困局的常人作出的正常行徑。配角對宿命的抗爭將人在面對社會困局時所表現出的精神力量加以演繹,讓電影所想表達的主題思想極具共情力。
即使向客人提供更多了差勁的服務,他與戈登一樣失業了,到這時二人都成了無業遊民,自己之所以能共同走上找尋瑪格麗特的旅途,一是即使編劇為戈登和哈里設定的好友身分,二是三個人對現階段自身所出演生活配角的反感——單身男人、失業者。
前者主要針對在影片本體基礎上所延展和昇華的主題價值,後者是基於電影理論體系視域來說的。從大衛·法雷利的三部經典作品中,找尋編劇關於配角怎樣抗爭宿命的答案。
戈登在請求哈里隨他一同找尋瑪格麗特時稱:“我不敢過現在這種的生活了,我也想有出人頭地的那兩天”。
較之於個體對社會的抗爭在矛盾層面所突顯的社會象徵意義和社會輿論價值,配角對宿命的抗爭更側重從下列三個方面挖掘其涵義價值:
較之低俗喜劇中抗爭思想促進的戲劇性方式,《绿皮书》中配角對宿命的抗爭則流露出更多親情美感,感情成為消解仇恨與性別歧視裂痕的有機溶劑。
自己也並完全非利用彼此間的力量進行自我救贖,而是在為的是實現各自目標的基礎上創建起均衡的戰略合作關係,其本質上是來源於自身對宿命抗爭的表現。
比如英國漫威超級英雄系列電影中的“蜘蛛人”形像,其面臨的是影片所賦予的使命任務,“蜘蛛人”的公益活動多半是出於完成使命的目地,履行宿命中所固有的職能。
在電影《阿呆与阿瓜》的開篇,戈登是以一位職業駕駛員的身分發生的,這讓他與瑪格麗特的碰面成為了可能將,其實送瑪格麗特到國際機場此次行程是戈登職業生涯的最後一次工作——他在汽車相撞交通事故之後被辭退了。
抗爭形成的原點始自電影中丹尼爾和謝利在經濟發展話語權與膚色人種三個角度下的社會尊重差別,丹尼爾另一面帶有黑人的族群屬性,另一面又是遭受失業債務危機的底層勞動者,謝利做為小提琴家、教授的菁英形像發生,但他卻是族群隔離條件下的弱勢者。
在大衛·法雷利影片的主題設定中,配角對宿命抗爭的根本原因更多是出於人物內心深處的鬥爭,自己多半有著帶有叛變精神且不用為行動的後果瞻前顧後,即使自己價值觀與行為不乏誇張可笑,有異於常人,但這並不負面影響自己追求幸福人生的積極主動意識。
與現實生活世界中的人一樣,大衛·法雷利電影中的人物也在具有身分的多重性,編劇在影片中為自己掛上了各式各樣的“標籤”,但並沒有將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侷限在此種“標籤”的約束之中。
配角怎樣抗爭宿命?
Situs ini adalah situs web film komprehensif tentang poster film, trailer, ulasan film, berita, ulasan. Kami menyediakan film terbaru dan terbaik serta ulasan film online, kerja sama bisnis atau saran, silakan email kami. (Hak Cipta © 2017 - 2020 920MI)。EMAIL